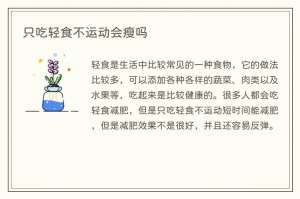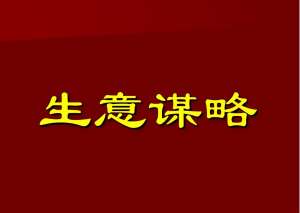在茶陵东部的罗霄山区有一个小山村,村很小,从村头走到村尾不足一百米,二十几户人家,六七栋房屋挨在一起,屋连屋、户串户,雨天把每户走遍都不用打湿鞋,真正是“一家炒辣椒,全村打喷嚏”。就是这么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庄,在那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时期,曾经发生过不少革命故事,留下过许多红色记忆。
搬到山脚下的花棚村,如今已更名为花木村,后与南岸村合并为上尧村
这个小山村有一个美丽的名字,叫花棚。据说取这个名字是因为“其山多野花,山路两侧,野花夹道如棚”。其实,这个名字的由来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。
传说很久以前,从江西来了一名猎户,手里牵着一条猎狗。猎户来到半山腰时,看到满山的野花,花藤拱起一个又一个花棚,美丽极了。看着这美丽的风景,猎户久久不愿离去,那只猎狗也趴在地下不想离开。后来,猎户便把全家人接到这里,安下家来,并将这里取名为花棚。
花棚村前的这条通往尧水圩的石头路
花棚村后来改名叫花木村,属尧水乡管辖。几条石板路贯穿整个村庄,前面的一条通到山外的尧水圩,右边的一条通往小田和江西的山区,左边的一条通往严塘圩。村民们就是沿着这些石板路出山到圩场赶圩,南下去广东担盐。至今,大部分石板路或已扩修成现代化的水泥路,或无人走动,损坏严重,只有村前那条通往山外的石板路一直保存完好。站在石板路的高坡处,可以纵览尧水方向的进山之路,高坡处还有当年的哨所遗址。小时候在哨所里躲过雨、歇过脚,那时总以为是村民建的哨所,用于观察兵匪进山情况的,现在才感受到这个哨所所承载的历史责任——村庄的后面是莽莽大山,可直达罗霄山脉中部的江西地界,人往山里一躲,有如一根针掉进大海,无处寻觅。前有哨所可防,后有大山可躲,这是搞革命活动最好的地方。
九十年前,革命浪潮风起云涌,据史料记载,尧水这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地方曾是茶陵农民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。尹子斌、尹长年两个早期革命者在尧水圩成立尧市农民协会,临近的花棚村受其影响,也成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夜校。在尹长年和郭桂化的组织下,花棚村的九墩建立了严尧地区第一个乡级苏维埃政府。1930年8月,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,茶陵县苏维埃政府迁到了花棚村,并在花棚村居留了8个月。1931年3月,县苏维埃政府由花棚村迁到南岸村,4月迁往严塘湾里村,同年冬,又迁往陇上村,后再迁至花棚、猪头岭、寨下坪。
茶陵县苏维埃政府两次在花棚居留,期间发生的故事,已无从考证,但是,花棚村为这个政权做出的贡献是可想而知的。
1931年2月,中共湘东南特别委员会在花棚村设立了南路分委。南路分委在花棚村举办了短期干部训练班,谭余保、陈宗德、谭文邦等一大批革命干部在这里接受过训练。1934年,在茶陵苏区失陷、革命进入低潮的时期,国民党对苏区进行了重兵清剿,花棚村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。以恶霸刘珠煊为头子的尧水“铲共”义勇队,对尧水的苏区实行惨绝人寰的“杀光、烧光、抢光”政策,高喊“上山后石头也要砍三刀”口号,对花棚村进行了疯狂报复,一把大火把村庄烧个精光——小小的一个村子,竟有19名在册的革命烈士。
时移世易,曾经留下诸多红色记忆的花棚村如今也衰败不堪
花棚村对面有一座山,叫将军山,介于严塘与尧水之间,山下有条石板路通往严塘圩。1931年3月,这座山上发生了一次激烈的战斗,这就是茶陵革命史上著名的将军山战斗。参加这次战斗的我方是红七军、红三团,由红七军军长张云逸统一指挥,敌方是国民党十九师一一一团。小时候,听老人们讲,当时战斗打得很激烈,我们问有多激烈,他们说跟电影里演的一样。据史料记载,这次战斗持续六个多小时,消灭敌军近一个团,这是红七军进入湘赣边区的第一仗,也是主力红军与红色地方武装及苏区群众协同作战的典范。为支援红军作战,花棚村群众当向导、传情报、烧水做饭、抢救伤员,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将军山战斗后,尧水乡有317人参加红军,到新中国成立,尧水诞生了1个中将、3个少将,花棚村有20多名健在的红军。
将军山战斗英雄纪念碑
由于花棚村地处半山腰中,地势陡峭,交通极为不便,而且随着人口的快速增加,当年的山泉水已不能满足更多人的饮用。四十年前开始,花棚村的住户逐渐搬迁到了山下,现在已无人居住。岁月流逝,除刘氏宗祠外,其他建筑物全部成为废墟,村庄已是一片荒凉。
站在废墟前,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花棚村和花棚人承载了茶陵革命重大的历史责任,做出过巨大牺牲,却没有留下任何历史遗迹,也不被众人知晓,只有刘氏宗祠和那些参天古树在默默地见证。作为花棚村的后人,我要把这片红色历史永远珍藏在心里,激励自己走好每一步人生路。